沙织
隐形委员会的《N°0公报》&本体论的无政府主义
译按
实际上,混乱就是生命。
所有的计划(如尼采所说)都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
——哈基姆·贝,《本体论的无政府主义》
这也正是隐形委员会在公报中所体现的,比如他们解释事情的思路,推进事业的方式,调动积极性的态度。所以说这个实验团体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幽默一如既往:一场认领作者身份、提供假证的骗局;一本真的是由匿名者写的《阴谋家宣言》;一个证明完毕的实证主义——他们叙述这些的时候找到了一种不受侵蚀、也丝毫不掺杂受害者情结的风格。
法西斯主义需要把它的种族清洗计划用于针对个人,包括心理层面,单单是展示一幅画亡族灭种的景象都是一种心理虐杀,因为,用德勒兹的话说,一个人身上至少也有15个部落。那么法西斯主义是否能按照提前制定的最精密的计划行事,丝毫不差地落实计划呢?换言之,像是隐形委员会的同志的处境,是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结果吗?是落入了敌人的天衣无缝的计划的结果吗?那个谎称是《革命将至》的作者之一的“男孩儿”,那个想把屎盆子扣在他们头上的匿名者写的那本“见多识广、无法反驳”的《阴谋家宣言》,等等,这些都是计划好的吗?那岂不是比隐形委员会聪明?不可能!如果这是一个计划,那它可是太虚幻、太失败了,大概迄今都不知道真正的作者。况且隐形委员会都说了,团体解散也不影响什么,他们自己就有一种分裂的思想,早就写下过《这不是一个计划》、《可怕的共同体》和《分裂的五十重阴影》(论证统一思想的普遍失败)等文章。
美国其实就有很多计划破产,这次它急于支援以色列就是印-以-欧通道计划受阻后的瞬间反应。
要攻击攻击隐形委员会,那些匿名者的内容丰富的密谋粪文根本就不需要思想,再长的文章都分两部分:因为理论A,所以毁灭B——毁灭自然、毁灭人类、毁灭一切他们想毁灭的。这种人十分希望别人进入和了解他们的世界,说什么区分食用菌和毒蘑菇虽然能避免危险,但也让人错过了解另一个世界中的欲望、激情、游戏的机会(所以呢?毁灭这个世界。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比如:第一部分罗列德勒兹书中的观点,从中人们知道自然和人工不是对立的;第二部分直接“毁灭德勒兹”。不为什么,跨度就这么大。他们证明完毕,能得出德勒兹处于统一对立的自然/意识形态结构中的结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一个他者的世界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和欲望革命的诉求。这就是为什么这时他们不会提如何形成一个无器官的身体,因为根本就理解、不进入、彻底错过了。密谋就完了,思想纯属陪衬。网上这种文章泛滥成灾,几乎是恐怖主义式的散布。这就像每当外交部一发言、央视一直播巴以冲突的访谈,评论区准有“美国不亡,天理难容/世界难安”。要知道有人已经论证“警察的终结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即便如此也不能就这样去灭绝警察,一是没这样的灭绝机器,二是只有经过革命资本主义才会终结,美国霸权也一样。眼下却有人仍只想召唤上帝。
所以隐形委员会这篇公报一上来就提出了汉娜·阿伦特的《对思想与道德的考量》。
&
“最终在21世纪的前25年消灭商品统治”
——Tiqqun-隐形委员会
这是最成功的一种无政府主义实践。只有在消灭商品统治的地方,人才夺回了自己的权利,彰显了自己的力量,瓦解了统治的阴谋。这个形式是很多样的,人们可以从驱动力的角度而不是表面的混乱形式中自己进行判断——让我们感到混乱的事情什么时候只是对商品的渴求和追捧,什么时候是暂时打破了现状和秩序,什么时候又是生命在诞生……在商品的统治中,智力和观点也都同一化了,几乎不可能单纯凭借一个人支持或反对某个社会事件的表态去看他的思想和立场,必须从他希望建立/为之努力的经济结构和对商品的观点上做出判断,比如他是要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是想打破贫富差距的壁垒进行横向联合还是想坚持一种从上到下的剥削压榨系统,再比如,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支持他所在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丝毫不能逾矩,那么他对巴勒斯坦人的援助又能怀着什么真实的好意呢,当他口口声声要为穷人的利益斗争时,他所说的穷人在哪儿呢?他和穷人在一起吗?资产阶级盲流的虚情假意就如同和野生猫科动物共处,结果就是,虐猫者被猫抓得鲜血淋漓,新伤覆盖着一层层旧伤;真正富有的人会像海明威那样,奔赴西班牙内战前线、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最后把基维斯特岛上的一栋白色小楼建成群猫的乐园,从此“海明威猫”享誉世界。
——这里为方便阅读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
Title: Communiqué N° 0
Author: comité invisible
Date: February 7th, 2022
Source: Retrieved on 2022-02-17 from
Notes: Translated by Ill Will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the-invisible-committe-communique-ndeg-0
http://illwill.com/communique-n-0
N°0公报
隐形委员会
思想的政治和道德意义只有在历史上那些罕见的时刻才会显现出来,当“事情分崩离析;中心无法维持/世界上只有无政府状态”,当“最好的人缺乏信念,而最坏的人充满激情”,在这些时刻,思想不再是政治事务中的边缘事务。当每个人都被其他人的行为和信仰不假思索地席卷时,那些能思考的人就会从隐蔽处被拉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是如此明显,从而成为了一种行动。
——汉娜·阿伦特,《对思想与道德的考量》
“隐形委员会”最初是19世纪30年代里昂的一个工人阴谋。在他的《拱廊计划》中,沃尔特·本杰明写道:“隐形委员会——里昂一个秘密社团的名称。”在2000年2月出版的La Fabrique版《布鲁姆理论》的结论中,有人写道:“隐形委员会:一个公开的秘密社团/一个公共阴谋/一个匿名的主体的机构,它的名字无处不在,总部却不在任何地方/幻想党的革命-实验的一极。”同一本书的封底在政治上更加明确:它将隐形委员会定义为“一个匿名的阴谋,从破坏到起义,最终在21世纪的前25年消灭商品统治”。通过“幻想党”,我们理解了,现在仍然理解,那些发现自己与商品的标志下的世界技术和人类学同一性发生冲突的人——无论是在公开的还是潜在的战争中,在分裂中还是在单纯的不满中。在这个同一的过程中,地球被构成为一个“连续的生命政治结构”,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冷漠的名字:“帝国”或“专制商品的世界”。在2022年,这些概念的通透性——或者至少是它们所证明的直觉——如果还能被人们忽视,那就后果自负吧!
在这种情况下,幻想党既是一个社会的盲点,也是一个不可言说的敌人。如今,这个社会只承认在其无可挑剔的程序中(指出那些)需要纠正的错误,以及急需粉碎的少数恶魔。然而,每当一场行动在幻想党中突然爆发成一个景观时,它立刻就会被谴责为某些“边缘少数人”的行为。当然,人们必须尽职尽责地避免承认,从此以后,有问题的边缘无处不在,而这个社会在假装吸收它的同时,会扩大对它的持续生产。“在统治将自身强化为对可见性的独裁和对不可见性的独裁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被抛回幽灵的不真实性中的幻想党,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了(Tiqqun 1,《关于幻想党的论文》)。同样真实的是,折磨这个社会的那种内心不满通常是如此沉默、分散和谨慎,以至于它往往会加剧其偏执狂的倾向——这是一种返祖的权力疾病,且往往是致命的。正如我们当时所指出的,“在一个偏执的世界里,偏执狂是对的。”
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疯狂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犯罪的观点,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一点一点地得到了证实,尽管所有的努力都是反向的,包括我们自己的努力。2001年9月,《Tiqqun 2》杂志的开篇就有这样的预感:“前面的短语将开创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将以越来越明显的方式被现实突然释放的威胁所笼罩。在某个时刻,‘隐形委员会’是这些页面中表达的内战伦理的名称。它指的是幻想党的一个特定派别,即其革命实验派。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措辞,可以避免一些对我们活动的性质和刚刚开始的时代可能说出的过分粗俗的废话。”(《内战导论》,Tiqqun 2)。正如预料的那样,2008年11月不乏“最粗俗的废话”,当时有十几人因“恐怖主义”被捕,给出的双重罪名是犯下一系列反核的破坏活动罪和写了一本由“隐形委员会”签名的《革命将至》。新闻界继续出色地展示了它是如何完成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任务的,全面接管了政府的捏造,也接管了反恐警察的捏造。它把自己弄得像个大傻瓜,这显然使它对自己和我们都一无所知。摇摇欲坠的大厦最终倒塌了,但在此之前,更广泛的公众就已经阅读了《隐形委员会》,代价是给所有相关人员带来了一些不便。如果有人仍然需要确认作者的概念在本质上是警察性质的——需要让某人对公开说出的真相“负责”——那么整个事件(制造出来)似乎就是为了提供确凿的证据。经过十年痛苦的诉讼,公诉机关的起诉书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聚焦在被控蓄意破坏并被怀疑是《革命将至》“主要作者”的人的身份上。出于自保的需要——我们从什么时候起欠敌人一个真相了?——导致其中一名被告在法官面前声称自己是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他在审判中不承担任何风险,也没有写过哪怕三行的《革命将至》和其他随后的书。在一个神秘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可以预料,这个谎言最终会被当作真理,而骗子最终会因为被当作真理而几乎说服自己。由于他就这样成为了被告们的发言人,这个男孩继续阐述了现代通信特有的自主化的结构性趋势,这让人们相信,只要在推特上有一个账号,一个人在智能手机后面就足以塑造现实。即使是管理当局也得提防让自己被这种幻觉的地毯绊倒——在任何情况下,发言人通常都不会对自己的言论有深刻的理解;这甚至可能对他们的任务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公众造成的痛苦没有被考虑在内。“隐形委员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团体,更不是一个“集体”。我们早就意识到“可怕的共同体”的危险。因此,它不受任何解散的影响,无论是面对法律的还是自愿的。它总是避免了威尔弗雷德·比恩在1961年描述的小团体的悲喜剧。另一方面,它却没有逃脱公众关注的痛苦。有多少人会因为“可能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可能再次”成为其中一部分,就会为自己带来神秘感?这种篡夺的风险,以及后者授权的整个伪装制度,是在这个黑暗时期采取匿名的少数不利因素之一。无论如何,这样的骗局只会愚弄愚蠢的人。隐形委员会列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党派情报,它们像碎片一样散落在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中间。显然,重要的不是成为它的一部分,而是工作本身,即收集碎片:在所有的一体化的整合策略中,保持一个显然在时间战争中失去的位置。“那么,还有谁能改变世界呢?那些不喜欢的人。”这已经是布莱希特1932年在库勒温普(Kuhle Wampe)的回答了。
隐形委员会的作用在于它是战略宣示的场所。那些以它的名字写作的人只有在经历了某种禁欲主义,某种去主体化的实践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实践剥夺了他们所有的防御机制,因为这些机制最终会塑造一个“我”:而他们放弃了自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设法做一些事情,不是“表达自己”,而是表达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发现的被悬置的东西,它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致命的。隐形委员会的文本是由直觉、观察、事件、匆忙中捕捉到的话语、进行中的实验和经历、完成或挫败的姿态、混乱的感觉、遥远的回声和收集到的公式组成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中的谁在这篇或那篇文章中写了压倒性的一部分是无关紧要的。无论谁在这个签名下写作,实际上都不是任何人,也不是所有人。在隐形委员会的那些持分裂立场的人中,所有的朋友都会对这种或那种单方面的提议、这种或那种的论点、这种或那种的看法进行辩论。简言之:我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抄写员,也就是说,是破坏事物现有状态的真正运动的抄写员。当这些文本没有任何作者的时候。这种方法似乎相当有效:20年后,很少有人能声称他们对自己时代的言论没有一句话可以收回,而且能够始终保持这样一种丑闻缠身的地位。“拒绝承认事物的状态是有效的,这是证明存在的态度,我甚至不会说那是智力,而是灵魂的存在。”(迪奥尼斯·马斯科洛)
最近出版了一本真正匿名的书《阴谋家宣言》,这本书在当代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为所有长期以来因隐形委员会迄今所取得的“成功”而蒙羞的人提供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复仇运动。这次公开私刑的信号是根据警方向《快报》提供的“信息”发出的——草率的侦探工作,随后截获并销毁了一家“有声望的”巴黎出版商的信件,这是一项不难再一次归因于DGSI(国内安全总局)的窥探工作。那些新闻奴才们勇敢地效仿,丝毫不记得他们以前在与狼群一起咆哮着反对隐形委员会时付出的努力收效甚微。在他们的运动达到高潮时,他们夸口说自己对《阴谋家宣言》一无所知,但首先他们会抱怨说,这本书在太多领域都见多识广,无法反驳——可怜的家伙!
最后,“少数派生命政治”甚至“通胀生命政治”的老派黑人党加入了这一行列,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失败恰好与他们站在帝国一边所取得的思想上的胜利相吻合。今天,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受邀前往梵蒂冈,与教皇方济各讨论他的全民收入慈善项目。至于“通胀生命政治”,在过去的两年里,没有人需要任何帮助来描绘其利害关系。“因为帝国最可怕的战略在于将一切反对它的东西扔进一堆丑陋的‘野蛮’、‘教派’、‘恐怖主义’或‘相互冲突的极端主义’中”(《这不是一个计划》,Tiqqun 2),我们失败的黑人主义幽灵和其他底层福柯主义者赶紧尖叫“混乱”、“法西斯主义”、“优生学”,为什么不来点儿——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否定主义”。毕竟,有问题的《阴谋家宣言》确实把实证主义搞得一团糟。QED(证明完毕)。然而,自黄背心运动以来,那些被事件进程所否定的人更愿意告诉自己,困惑的是起义自身,而不是他们。他们随处可见的“法西斯主义”只是他们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因为这会让他们变得正确,如果不是智力上的,那么就是道德上的。然后,他们将有机会最终成为他们梦想中的英雄受害者。那些在历史上放弃战斗的人更愿意忘记,这个时代的战争也是在思想的地形上进行的——顺便说一句,如果没有思想,福柯就不会从纳粹和行为主义的设计师那里夺取“生命政治”。至于认为有一种革命是披着纯洁外衣的,或者认为正是通过增加道德上的诅咒、政治上的预防措施和文化上的势利才击败了反革命——我们把这一切都留给了帝国左派。后者只是谴责自己,在其卫生警戒线和预防措施后面等着腐烂,紧紧抓住它所认为的政治资本积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言论逐渐向统治者的言论倾斜。
至于我们,我们更喜欢进攻,也更喜欢投篮。
我们更愿意交战。
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
Hakim Bey
Ontological Anarchy In a Nutshell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hakim-bey-immediatism
哈基姆·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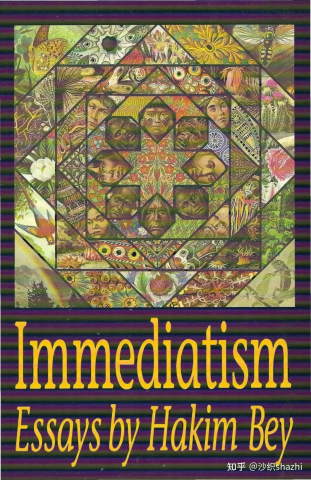
由于绝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以任何真正的确定性来预测“事物的真实本质”,所有的计划(正如尼采所说)都只能“建立在虚无之上”。然而,如果必须有一个计划——这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抵制被归类为“虚无”。出于虚无,我们将有所发明:起义,反抗宣称“事物的本质就是这样的”的一切。我们不同意。我们是不自然的,在法律的眼中,我们是微不足道的——神圣的法律、自然的法律或社会的法律——任你选择。我们将凭空想象我们的价值观,通过这种发明行为,我们才能生活下去。
当我们对“无”进行调解时,我们注意到,尽管它无法被定义,但矛盾的是,我们可以对它说些什么(即使只是隐喻性的):——它似乎是一种“混乱”。无论是作为古老的神话还是作为“新科学”,混乱都是我们研究的核心。大蛇(提阿玛特、巨蟒、利维坦),赫西俄德的原始混沌,在所有国王、牧师、秩序、历史、等级制度和法律的代理人面前,主持着旧石器时代的漫长梦想。“无”开始呈现出一张面孔——混沌先生光滑、毫无特色的蛋脸或葫芦脸,混乱变得越来越严重,混乱变得过度,虚无向某物慷慨倾注。
实际上,混乱就是生命。所有的混乱,所有的色彩,所有的原生质的紧迫感,所有的运动——都是混乱。从这个角度看,秩序(反而是)死亡、停止、结晶、异样的沉默的表现。
多年来,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声称“无政府状态不是混乱”。即使是无政府主义似乎也想要一种自然法则,一种内在和天生的道德,一种存在的意愿或目的。(在这方面并不比基督徒好,或者尼采是这么认为的——激进只是因为他们的怨恨之深。)无政府主义说“国家应该被废除”,只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更激进的秩序。然而,本体论无政府主义回答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混乱中“存在”,除了混乱的主张(然而,混乱是不确定的)之外,所有本体论主张都是虚假的,因此任何形式的治理都是不可能的。“混乱从未消失。”任何形式的“秩序”,如果不是我们为了自己的庆祝目的而在纯粹的“存在自由”中想象和直接自发地产生的,都是一种幻觉。
当然,幻觉会致命。惩罚的画面萦绕在秩序的睡梦中。本体论无政府主义建议我们醒来,创造我们自己的一天——即使是在国家的阴影下,那个沉睡的巨大脓疱,其秩序之梦也会随着壮观的暴力痉挛而转移。
唯一足以促进我们的创造行为的力量似乎是欲望,或者查尔斯·傅立叶所说的“激情”。正如混沌和厄洛斯(以及地球和古夜)是赫西俄德的第一个神一样,人类的努力也不会发生在他们的宇宙引力圈之外。
激情的逻辑导致了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国家”都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命令”都是虚幻的,除了欲望。没有存在,只有变化——因此,唯一可行的政府是爱或“吸引力”。文明只是隐藏在一层薄薄的、静止的理性面纱背后——只有欲望才能创造价值的真理。所以,文明的价值观才建立在对欲望的否定之上。
资本主义声称通过欲望的再生产来产生秩序,但它实际上起源于稀缺性(缺失/匮乏)的生产,只在不满足、否定和异化中再生产自己。随着景观的解体(就像一个故障的VR程序),它揭示了商品的无肉之骨。就像爱尔兰童话故事中那些出神的旅行者一样,他们访问了另一个世界,似乎在吃超自然的美味佳肴,我们在朦胧的黎明中醒来,嘴里含着灰烬。
个人vs群体——自我vs他人——这是一种通过控制媒体,尤其是通过语言传播的错误二分法。赫尔墨斯——天使——媒介是信使。所有形式的交流都应该是天使——语言本身也应该是天使——一种神圣的混沌。然而,它感染了一种自我复制的病毒,一种无限的分离的晶体,一种阻止我们一劳永逸地杀死Nobodaddy(nobody和daddy的合成)的语法。
自我与他人相辅相成。没有绝对范畴,没有自我,没有社会——只有一个混乱复杂的关系网——还有“奇怪的吸引力”,吸引力本身,它唤起了生成过程中的共鸣和模式。
价值观产生于这种动荡,价值观基于丰富而非匮乏,礼物而非商品,以及基于个人和群体的协同与相互增强——价值观在各个方面都与文明的道德和伦理相反,因为它们与生而非死亡有关。
“自由是一种精神动力技能”——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国家”——一场运动,而不是一种治理形式。死亡之地知道完美的秩序,从这个秩序中,有机的和有生命的都在恐惧中萎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打滑的文明有一半以上的人喜欢安逸的死亡。从巴比伦和埃及到20世纪,权力的建筑永远无法与墓地的土葬区区分来。
游牧主义和起义为我们提供了本体论无政府主义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模式。当我们把文明和革命当成战争的形式,当成陈旧的巴比伦战争的变体,当成匮乏的神话,我们就不再对它们的完美无瑕感兴趣了。像贝都因人一样,我们选择了一种皮肤的建筑,以及一个充满消失之地的地球。就像公社一样,我们选择了一个欢庆和冒险的流动空间,而不是工作棱镜(或监狱)的冰冷浪费,失去的时间的经济,对合成的未来的怀旧之声。
乌托邦诗学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欲望。乌托邦之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批判理论,这种理论无论是实践政治还是系统哲学都不可能发展。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仅仅局限于将乌托邦视为“无处可去”,同时哀叹“欲望的不可能”的理论。奇妙的事物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情境”的创造——属于“物质的身体原则”,属于想象,属于当下的生活结构。
意识到这种直接性/即时性的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快乐的范围,只需从“幽灵”(施蒂纳称之为所有抽象)的催眠中醒来;“犯罪”可以完成更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自我在快感方面的加倍。从施蒂纳的“自我拥有者的联盟”,我们继续进入尼采的“自由精神”圈子,再到傅立叶的“激情系列”,不断地将我们自己加倍,就像他者在群体的爱欲中把自己加倍一样。
这样一个群体的活动将取代我们这些可怜的波莫(PoMo)混蛋所知道的艺术。无端的创造或“玩耍”,以及礼物的交换,将导致艺术作为商品再生产的消亡。“达达认识论”将融化所有的分离,并将一种古政治学给予新生的精神通灵,其中生命和美不再能够区分。在整个高等历史中,这个意义上的艺术一直被伪装和压抑,但从未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一个最受欢迎的例子是:绗缝蜜蜂——由一个无等级的创造性集体自发完成的图案制作,目的是生产出一种独特、有用和美丽的物品,通常作为礼物送给与该圈子有联系的人。
即时主义组织的任务可以概括为扩大范围。我的生活中有越多的部分可以从工作/消费/死亡的周期中解脱出来,并(重新)转向“蜜蜂”的经济活动,我获得快乐的机会就越大。一个人冒着一定的风险,从而挫败了机构的吸血鬼能量。但是风险本身构成了快乐的直接体验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在所有起义的时刻——所有构成强烈的冒险乐趣的时刻——起义的节日聚会方面,节日的起义性质中都有体现。
但是,在个人的孤独觉醒和反抗集体的协同记忆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社会形式,为我们的“计划”提供了一些潜力。有些只不过是两个志趣相投的人之间的一次偶然邂逅,他们可能会通过短暂而神秘的邂逅来扩大彼此;还有一些像假日,还的有一些像海盗乌托邦。似乎没有一个能持续很长时间,但那又怎样?宗教和国家吹嘘他们的永恒——我们知道,这只是摇摆不定中的空话……他们的意思是死亡。
我们不需要“革命”机构。“革命之后”,我们仍然会继续漂泊,以逃避复仇的政治的瞬间僵化,转而寻找过度的、奇怪的……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成为唯一可能的常态。如果我们现在加入或支持某些“革命”运动,那么一旦他们“上台”,我们肯定会第一个“背叛”他们。毕竟,权力是属于我们的,而不是什么该死的先锋派。
在《临时自治区》(Autonomedia,NY,1991)中,有一个关于“作为消失的权力意志”的讨论,强调了“自由”时刻的回避性和模糊性。在目前的一系列文本中(最初在纽约一家调频台以Radio Sermonette的形式呈现,由无政府主义自由意志图书俱乐部以该名出版),重点转移到了重新出现的实践理念上,从而转移到了组织问题上。对群体美学理论的尝试——而不是社会学或政治学——在这里被表达为自由精神的游戏,而不是制度的蓝图。作为媒介或异化机制的群体,已经被致力于克服分离的即时主义群体所取代。这本书可以被称为关于节日聚会的思想实验——它没有更高的野心。最重要的是,它并不假装知道“必须做什么”——这是准政委和大师的错觉。它不想要门徒——它宁愿被烧死——献祭而不是效仿!事实上,它对“对话”几乎没有兴趣,更愿意吸引同谋而不是读者。它喜欢说话,但这只是因为谈话是一种庆祝,而不是一种工作。
在这本书和沉默之间,只有陶醉。
——哈基姆·贝
(1993年春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