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织
躯体的消失:战争、观众、超雄体综合征

侵略、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往往以罪与罚为名义,目的却只是为了让一种新的悲伤在人类中蔓延。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知道,战争毫无神圣性和光环可言,要联合战争还是反对战争、鼓吹战争还是结束战争,全看它是否对自己的地缘政治有利,看它是否能限制竞争对手,一个还堪称国家的国家,并不能以建立一个普适的全球秩序为目标,它的目标是维持自己的秩序,不被渗透和操控,在所有国家中立于不败之地。无能的民主党虽然更多地流下了鳄鱼的眼泪,然而正是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爆发了新一轮的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国国内也是一团乱,这说明它已经失控。
重点来了。抄袭批判,以为把对战争的批判反馈给战争,叠加到它之上,就能将战争神化,这是观众的游戏。这类观众的“批判”不是为了反对俄国、以色列,而是为了让普京、内塔尼亚胡成神。我们经常在理论口碑倒了的知乎用户那里看到的也正是这种观众,将自己的肉体排除、虚无化、精神化、抽象化也智能化的观众。他们真正地召唤战争,仿佛对肉体进行这种转化后,他们自己就在战争中刀枪不入、成为战争的例外了,仿佛这样一来战争就能站在自己一边,使其顺应自己的意志、符合自己的目的、与自己的方向一致,为己所用。表面上看,神化战争的人分享的是国家的逻辑,而其虚伪的批判分享的是无政府主义的话语,但他们两者都不是,他们只是生命之敌,是全球秩序和总体战争观念的真正代表。也就是说,最没有影响力和原创力的人,乃至有智力缺陷的盲流和丑胎,摇身一变成了人们头脑的代表,企图空手驾驭一切。将战争神化这种事难道不是最卑贱、最空洞、最不提供价值的人的发明吗?在进行这种发明之前,他们不已经是非存在了吗?所以,观众是第一个被战争团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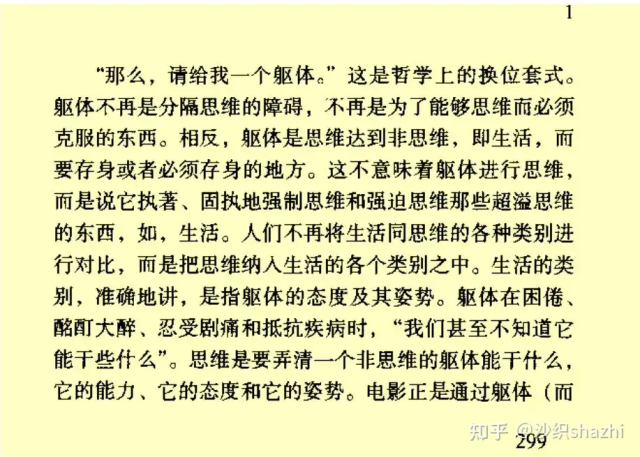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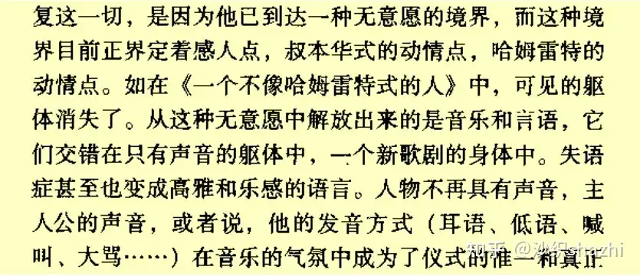
“给我一个躯体”是德勒兹《时间-影像》第八章“电影,躯体和大脑,思维”的起始句,也贯穿了整章。狂欢节、化装舞会、怪诞身体都以一种非思维的方式、一种姿势,展示仪式或态度,这是超思维,所以躯体的消失作为一种态度亦可分析。从道德主义的角度看,躯体总是不道德的,然而没有什么是比躯体的消失更耻辱的。
有一个躯体才能让超出了思维的生活得以被思考。所以戈达尔会说如果读一本小说时脑子里有图像,那他就是一个糟糕的电影人。他根据小说拍的电影和小说原著完全不同,而且他认为好的小说无法拍成电影,所以他选的是他认为有缺陷的小说,这种缺陷是他电影的底层结构。摄像机本来就架设在日常躯体之上,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同样也“昭示了集中营”(戈达尔语)。这并不代表躯体即“免疫漏洞”,为悲伤而存在,可以成为思维的客体;相反,没有躯体也将没有任何生活感受,其大脑、思维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和主体性。用躯体的消失逃避躯体的人是没有任何优越性的。男权主义的盲目优越感建立在男性躯体和女性躯体的绝对对立和割裂上:作为人类,最好不要有一个女性躯体,因为它总被客体化,男性躯体则已然意味着无往不利。对“超雄”患者的恐惧和污名化反应的就是对绝对男权的身体的恐惧,这也说明,有一个躯体是全球右倾时代的恐惧。极右翼的倡导就是:最好不要有一个躯体,哪怕是男性躯体。然而男权主义难道不是一个幽灵吗?极右翼骷髅难道不就意味着一个不能思维的色情狂吗?“无政府主义如何看待超雄体综合征”,这个问题不如换成如何处理“女性有一个躯体”?这个时代能出现这个成问题的问题,那是谁的悲哀?不要把某个患者视为超雄体综合征,把法西斯主义视为社会超雄综合征或天生坏种就可以了,就这么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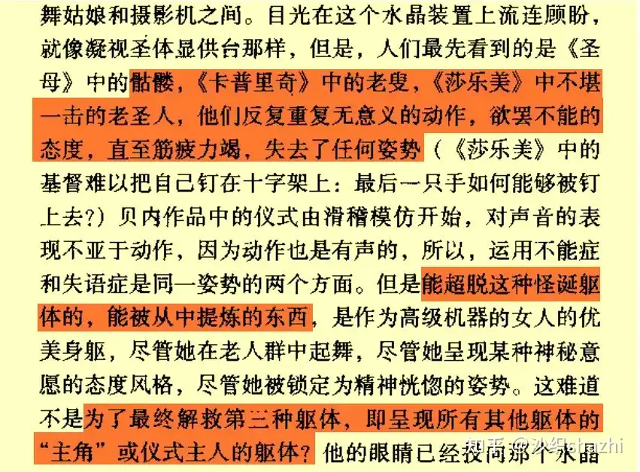
最后,人类思维的进展就是由躯体态度驱动的(而躯体态度恰恰不能在小说和语言文字中寻找和观看到,有时甚至眼见也不能为证,例如抑郁症患者可能看起来很欢快,因而姿势的发明对电影的眼睛来说特别重要),对女性躯体的污名化,其实是对思维和大脑的抨击,这大概意味着法西斯自己丢了脑袋,“精疲力竭,失去任何姿势”,而且,它的“超雄”和“神圣”也不再有什么救赎。思维活动的自主权和无国界在法西斯看来是道德危机,应对这一危机的策略是诽谤躯体。必须得说,法西斯的暴力仍然不能抵抗思维的暴力。躯体的(非)思维或思维的无器官的身体令既定秩序感到绝望。
或者说思维是生殖者,或者没有大脑没有爱。就是这样,法西斯还能怎样?因为感到基督教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被亵渎了,某赞助商才跑路。全世界得罪不起基督教,但艺术家无所谓。但现在来不及了,基督教已在全世界、全球面前裸奔过了。无论哪个国家的艺术家去巴黎导演这场开幕式也未必不亵渎基督教,它只是时间到了。但基督教还有道德优越感,还有!利用自己的腐败优越,皇帝的新衣管用。基督教来到了它的自渎阶段。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发展而来的法西斯主义也只能自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