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织
从网络左派到新法西斯的过渡
-
一个唯一会游泳的人在一堆落水者中选择救谁不需要成为良心问题,在打打杀杀者中选择护谁也随便,因为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爱一个人要用杀死别人的决心来证明和助力(当然这种计划并不会采用这么露骨的语法),就是说为什么对雅利安人的爱需要在屠杀犹太人时得到表达?
-
爱不需要借助这种途径来表达。所以,如今我如何判断新法西斯呢?一个人需要将和自己有关联的人视为一个禁锢的存在、一套禁锢体制本身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渴望,这个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伪装在压抑下的合乎流程、合乎惯例、合乎建制与习俗和政治面貌的日常活动,一旦到了临界点,就不得不爆发“纯种德意志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当网络左派在回答“如何反驳军训有用论?”时,就已经表明了这种冲突的萌生。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网络左派那里意味着:在军训这件事上有没有叛逆一下的价值?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其回答要从规训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控制社会已经俨然区别于规训/惩戒的社会了,随着这种转变,作为国家规训的社会层面的军事训练早就不是军训的形式。“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普遍性的市场。而市场并不制造普遍,并不制造均衡。这是一个疯狂地制造财富和苦难的工厂。”(德勒兹)所以,“军事的存在”与假惺惺的、装腔作势的、散发着冲天臭气的、恐怖的和平以及这个商品社会、编码的“高尚工作”为一体,与上进经济和《红死魔的面具》(爱伦坡的一篇小说)中的化妆装舞会的娱乐动员为一体。这才是真正迂腐的如19世纪一般落后的当代军训的面目。
-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堂而皇之地用规训答题的互联网左派用户,同时也会是这样一个庸人:他觉得光是xxxxx不够爽,一边给周围的人下毒一边偷偷xxxxx才本领高强、英雄盖世(匪夷所思,如此来做英雄)——因为他满心认为周围的人都是只能被他爱或不爱,被他选择或放弃,不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爱以及被高贵的方式所爱的人,就好像人们不配有出口。好比说,不是说那里有个封建社会,制定了一套封建禁锢制度,所以要推翻它,要把人们从中解放出来,而是说有一种杀死某人的需要,通过参与偷偷xxxxx来引入封建社会与自由渴望的矛盾,然后把谋杀对象等同于一整个封建社会的存在,这样就有了直接杀人的动力乃至借口。
-
——在把他人视为一个禁锢的存在的时候,人们已经是种族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因为否定了其主动去爱的能力和以其他方式被爱的可能性,当情况升级,所谓的欲望和对自由的召唤就必须让屠杀、消灭成为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像欲望-机器这样的德勒兹概念没有得到理解和尊重,反而被利用到最保守和反动的地方。
- 在这个时代,存在禁锢的行为、禁锢的律令,但是有没有一个为禁锢而存在的主体呢?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不是一个为禁锢而存在的人呢?难道新法西斯不是想要一个超级全球自由流动市场,非但不会限制妇女的流动,反而会设法使其蒸发在流徙、“交换”和“更新迭代”的途中吗?
- 要轰击,就要有个靶子,无论这个靶子存不存在,直到轰击实现,如果有必要,轰击要在假靶子面前持续进行,它让比如说“禁锢”成为一个在“事实”上存在的选择进退的尺规,用福柯的还说就是成为一套真理叙事——这就是辩证法。
-
其实,当福柯指出人们通过谈论性的问题来阐发禁锢和权力的问题,这件事是复杂的,或者指出我们已经脱离惩戒的社会进入控制社会时,他是要人们注意——立刻杜绝辩证法继续横穿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指出这是辩证法的应用和实践。辩证法是贱民的艺术,一字不差。
-
关于我们已经脱离规训社会这个观点,可以参考《哲学与权力的谈判》中德勒兹的陈述:
我们肯定是在进入“控制”的社会,这些社会已不再是严格的惩戒式的社会。福柯常常被视为惩戒社会极其主要技术——禁锢(不仅是医院和监狱,也包括学校、工厂、军营)的思想家。实际上,他是最先说出此话的人物之一:惩戒社会是我们正在脱离的社会,是我们已经不再置身其中的社会。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巴勒斯已开始了对此的分析。当然,人们仍在不断地谈论监狱、学校、医院,这些工具已陷入危机境况。但是它们之所以陷入危机境况,正是因为它们陷在后卫部队的战斗中。P199 *****
-
法西斯在快感中屠杀时意识不到那是罪行,也感觉不到它造成的伤害,纳粹只知道希特勒是他们的英雄,即便在这种英雄状态中,他们也身在地狱般的压抑,这和当今网络左派的精神状态何其相似;但是革命对法西斯的制裁手段会是一种明朗的快乐,一种快乐的原则,乃至可以抵偿金钱和剥削压榨。这是为何?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欲望是革命的,但对纳粹的审判不过是处决了几个战犯。所以,不但德勒兹说的重建一种法律的哲学是重要的,而且从中诞生一种哲学的刑法更加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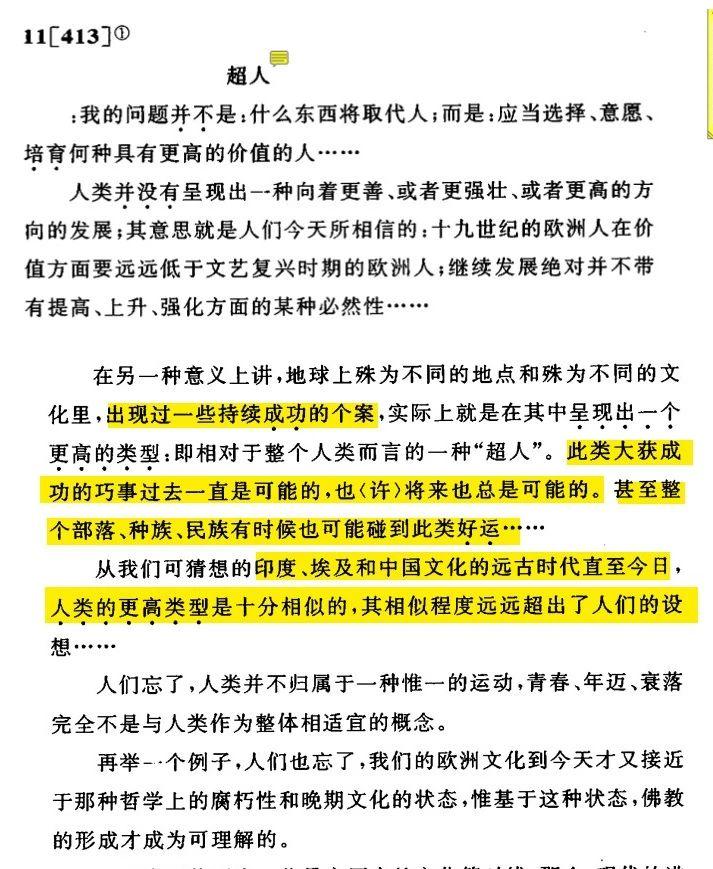
-
就是在这里,我想到尼采对罗马帝国的高度评价。也许他就是从建立一种法律的哲学的角度“回忆”起古罗马的,正如但丁在《神曲》中踏上旅途之前,面对维吉尔的“不可靠”的激励召唤缪斯,回忆起了埃涅阿斯。
-
事实上,谎言随着人们说谎的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说谎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持,也可能是为了毁灭。人们可以把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请理解为当今的网络左派]看做是一丘之貉,因为他们的目的,他们的本能就只是为了毁灭。要证明这个命题,有的是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以其令人惊奇的明晰性显示了这种证明。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宗教立法的目的在于把促使生命繁荣的最高条件“永恒化(verewigen)”,也即把社会的最大组织“永恒化”,那么,基督教则认识到必须要把终结这种社会组织当做自己的使命,因为在这种社会组织当中生命会得到繁荣的发展。在那里,经过长期的试验和风险之后,理性所获得的收益是要被投资下去的,并且还希望这种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还应该尽可能变得更大、更丰富、更独立些。但是,在这里,却恰恰相反,收获在一夜之间被毒害了。……那高高屹立着的罗马帝国,和所有在它之前、在它之后所达到的东西相比,和所有拙劣的、半吊子的东西相比,都是历史上最宏伟的组织形式,尽管当时的条件非常困难。可是,那些神圣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请理解为当今的网络左派]却炮制出了“虔诚”来毁灭“世界”,也就是来毀灭罗马帝国,直到它片瓦不留,直到日耳曼以及其他粗野的民族可以成为它的统治者为止。…… 基督徒和无政府主义者们[请理解为当今的网络左派],这两种人都是颓废的,都是无能的,对所有事物,他们除了分解、毒害、耗竭和吸血以外,再也无所作为。他们的本能恨死了所有现存的事物,所有伟大的事物,所有能够久经时间考验的事物以及所有给生命许以未来的事物。……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吸血鬼(Vampyr)。在一夜之间,它毁弃了罗马人那些伟大的作为,——这些罗马人曾经赢得了获得一种伟大文化所需要的基础。
-
——(尼采,《反基督》)§58
- 归根结底,倘若尼采曾有那么几个短暂的瞬间认为不但罗马,而且埃及、印度和中国文化的远古时代曾出现过大获成功的人和制度的案例,也就是超人——一个庶民,一个崇高的意象和现实接合,在建制上得以实现,而不仅仅是一首诗,例如史蒂文斯的《一个睡在他自己生命中的孩子》,这个孩子在一群老人中间是他们唯一的皇帝——那么他指的不仅仅是在他之后超人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而且在他之前,超人曾实现一种法律的哲学。可想而知,法西斯在罗马会感受到制裁,不仅仅是得到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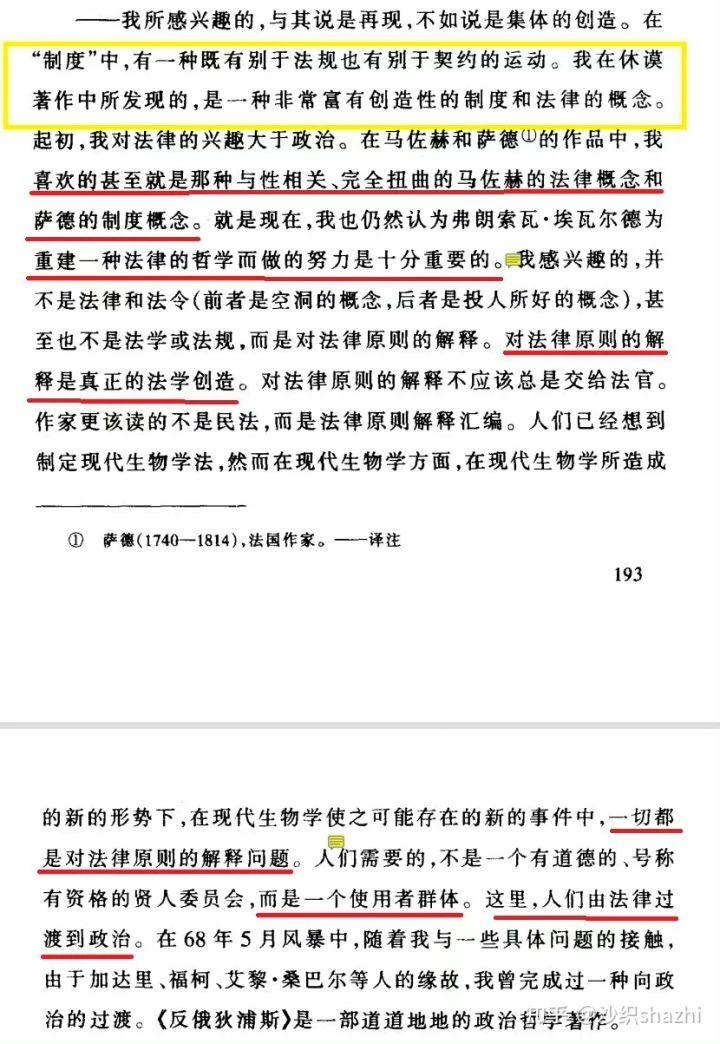
-
尼采深刻地认识到,惩罚和奖赏在今天都全部失去了意义,如果要谈禁锢以及打破禁锢的使命,那无疑是相当虚伪和可笑的,就像在网络上大呼小叫的左派和黑格尔主义者那里发生的。
-
倘若今天还有一种有意义的禁锢,那它反倒可能和玛丽莲曼森一样美妙,德勒兹确实说过:“面对即将出现在开放环境中的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仿佛是美妙而亲切的回忆。”这句话有可能非常有内涵。在有伟大的政治的地方,也许确实存在伟大的禁锢。但是我之所以认为在一种法律的哲学的意义上禁锢不是个更好的切入点,是因为比起禁锢,流放法是更具情状和意义的,有更多的发明创造的痕迹。而且古代希腊和罗马对政治犯罪采取的手段,流放更多,似乎主要是流放。即便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在那个时代,监狱也还不是直接与法律的执行挂钩的,而是临时限制一个统治者或政敌的军事行动的地方,一个进行有时限的审讯的地方。终身监禁作为一种惩罚,这是如何可能的?这种惩罚并不抵偿人们的损失和所受到的伤害,而单纯是在语法和定义上让犯罪这一行为有所对应。就像尼采说的,失去了意义;或者用史蒂文斯的诗句来说:心不满足。
- 但是古代的流放则不然,希腊罗马的名人,中国古代的名人,他们因为被流放而出名。流放,想必曾是个有意义的好主意,虽然它会被用来使坏。参考那些被冤死在流放途中的名人,流放有很强的情感强度在里面,流放的空间被情感的内容填满,正如神的暴力(本雅明)——尤其在那些确实该被流放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奥古斯都对自己的刺客女儿的流放。如果一种从法律的哲学出发的刑法获得了意义,承担着情状——打比方说,奥古斯都判处你被流放,使心得到满足,使法西斯对皇帝所受到的伤害感同身受,那么又何须基督教的地狱呢?
-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一开始就做出的回答:
-
如今我如何判断新法西斯呢?一个人需要将和自己有关联的人视为一个禁锢的存在、一套禁锢体制本身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对自由的渴望,这个过程往往还伴随着伪装在压抑下的合乎流程、合乎惯例、合乎建制与习俗和政治面貌的日常活动,一旦到了临界点,就不得不爆发“纯种德意志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