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织
当神圣邪恶bot们谈尼采:狄奥尼索斯,觉醒
《谢林与尼采:释放爱之神》https://zhuanlan.zhihu.com/p/667487983
作者:零食喜欢吃
这篇文章这么谈尼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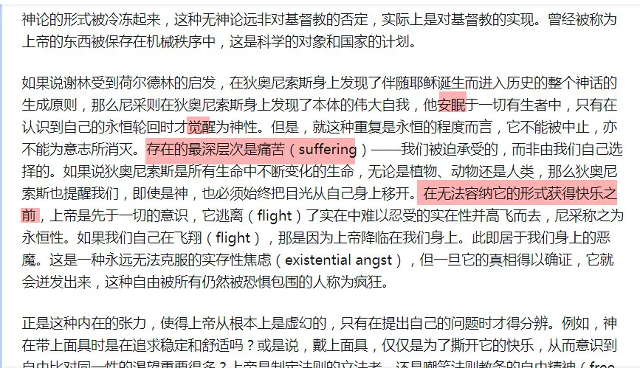
作者把存在或狄奥尼索斯精神解释为“存在的最深层次是痛苦”,简直逆天,他难道不是狂欢之神、庆祝之神、葡萄酒发明家吗?
狄奥尼索斯并非“安眠”在一切有生者中,他是活跃在一切有生者中的醉,有生者无法容纳快乐?痛苦比快乐来得早、来得快?狄奥尼索斯在尼采哲学里意味着要让有生者从凡人变成神?
尼采认为快乐比痛苦更原始,痛苦是快乐的一个结果:
《权力意志》14[24]
人们可以看到,本书 把悲观主义、更直白地讲就是虚无主义,视为“真理”,但并没有把真理视为一种最高价值,更没有把奠理视为最高权力。
在这里,作者认为,求假象、求幻想、求欺骗、求生成和变化的意志要比求真理、求现实性、求存在的意志更深刻、更原始、“更形而上学”——后者本身只不过是求幻想的意志的一个形式。同样地,快乐被视为比痛苦更原始的, 因为痛苦是有条件的,只不过是求快乐的意志(即求生成、增长、赋形的意志,因而也就是求征服、求抵抗、求战争、求毁灭的意志)的一个结果。作者构想了肯定此在(Dasein)的最高状态,这种状态甚至把痛苦、形形色色的痛苦,也永远当作提高手段包括在内了,那就是:悲剧的——狄奥尼索斯的状态。
说狄奥尼索斯在安眠着,那是完全睁着眼说瞎话,狄奥尼索斯是一股强制狂欢的力:
《权力意志》14[36]
艺术本身作为人身上的一种自然力量出现在两种状态中,不管人是否愿意,它都支配着人。一方面是幻觉强制力,另一方面是狂欢强制力。这两种状态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只是更为虚弱些,诸如在梦与醉中,犹如在……
然而,同一种对立依然存在于梦与醉之间:两者都能把我们身上的艺术力量释放出来,但各不相同。梦释放出观看、联结、创作的力量;醉释放出神情、激情、歌唱、舞蹈的力量。
——所以给《谢林与尼采:释放爱之神》点赞的人其实是在点踩吧?这文章难道是用ChatGPT从各种抄来?竟可以将狄奥尼索斯与“存在的最深层次是痛苦”、“在无法容纳它(快乐)的形式获得快乐之前”、“安眠”、“觉醒”融为一体。狄奥尼索斯需要在你们身上觉醒!
接上面的引文。这不是说狄奥尼索斯的普遍存在是作为一个狂欢的典范或者是领头的善舞者,而是作为理念和自然的运动:狄奥尼索斯式的理念(《差异与重复》p464)——“在已然被完全微分了的未分化中,在这奇异的前个体状态中,存在着它那永远不能被平息的迷醉一一哲学家正是运用这作为双重色彩的清楚一模糊,并动用一种微分的无意识的全部威力来描绘世界。”
理念的这种运动就是时空动力的戏剧,也就是绝对差异和发散系列。因而舞台上的人尽管扮演多种角色,角色还叠放成一挂,但这些角色有一种内部空虚,对尼采来说,狄奥尼索斯被纳入角色,这种空虚就被填充了,这就等于将真实运动的无限引入这种堆放,换言之,填充了自然和表象。在此之前,形而上学是不会运动的,它只是一个收敛的共时系列,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如果一个人是国王,他就还不是动物,尽管国王和动物都作为一个单子表现世界。发散系列是指一个国王身上不但有动物,还有植物、矿石、钻石,它们并非同时降落于他的,不共时因而让系列发散了。这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在重复中改变了自身。不是谁应该重复狄奥尼索斯,而是当人们因差异而重复、而发生戏剧时,就已然进入狄奥尼索斯的原则——真实运动的无限和形而上学的理念没有性格,直到它被赋予狄奥尼索斯的性格。如果你重复,那是因为痛苦作为你需要提高的一个信号,而背后的动力是迷醉。狄奥尼索斯作为一种生理的、心理的、动力的解释学,和基督教神学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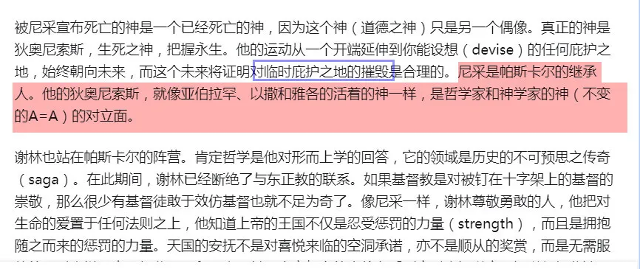
作者继续说狄奥尼索斯对于尼采就像上帝对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是继承了帕斯卡!尼采怎么继承帕斯卡了?他在《权力意志》中说:
11[408]
最悲惨的例子——帕斯卡尔的堕落,后者相信原罪败坏了他的理性:而实际上他的理性只是通过基督教而被败坏了……
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其实是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的材料,这不是一个和燔祭有关的主题,而是超验所牵涉的相关项的问题:在对法则的抗辩与顺从中,亚伯拉罕重复了对以撒的爱,后者的燔祭被天使及时阻止,在犹太列祖中,以撒是最长寿的一位祖先。然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不同的,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说:
约伯是无限的抗辩,亚伯拉罕则是无限的顺从,但这无限的抗辩与无限的顺从完全是一回事。约伯以反讽的方式对法则提出了置疑,他拒斥一切派生的解释,而且为了达至那作为原则和普遍者的最为奇异者,他还废黜了一般者。亚伯拉罕以幽默的方式服从法则,但他恰恰在这种服从中重新发现了他独生子的奇异性,而法则责令他以之献燔祭。正如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那样,重复是作为心理意图的抗辩与顺从共同的超验相关项。
在尼采那熠熠生辉的无神论中,法则之恨与amor fati [拉:命运之爱]、好斗与赞同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双重面孔,他既继承了《圣经》又转而反对《圣经》。此外,我们发现查拉图斯特拉还在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与康德竞争,与道德法则中的重复之考验竞争。p18
我们并不认为在尼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克尔凯郭尔的上帝之间有任何类似性。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或者相信二者之间有不可逾越的差异。不过,更为要紧的问题是:尽管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构想这个目标,二者在重复这一主题上的巧合,在这一基本目标上的巧合是从何而来的呢?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属于那些给哲学带来了崭新表达方式的哲学家。人们乐于谈论他们对哲学的超越。然而,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运动才是真正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批评黑格尔,就是因为后者所理解的运动仍然是虚假的运动,是抽象的逻辑运动,亦即“中介”。他们想要让形而上学运动起来、活动起来。他们想要使它进入现实状态,进入直接的行动状态。p20
作者暗搓搓地援引克尔凯郭尔,是想说狄奥尼索斯和克尔凯郭尔的上帝一样残暴,总是摧毁人的“临时庇护地”,或者摧毁那些爱上帝上的人。换言之,狄奥尼索斯有待摧毁自己。但克尔凯郭尔的上帝并没体现残暴。他们两个的神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思想和情感运动起来。
不过狄奥尼索斯确实涉及到一种“毁灭”——
《权力意志》2[25] [19]
“你在我看来心怀叵测”,我有一次对狄奥尼索斯神说,“就是要把人毁灭掉么?”——“也许吧”,这个神答道,“但却是要让我能摆脱掉什么”。——“是什么呢?”我好奇地问。——“你应该问是谁呢?”狄奥尼索斯如是说,然后就沉默了,以他特有的方式,也就是引诱性地。——你们或许要就此来观察他!那是春天时节,万木生气勃勃。
这就涉及到一种沉默修辞学。正如我在《诗山也在崩塌》(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044864650969316)中说的:
狄奥尼索斯是经常沉默的,通俗说,他只在一首诗中发声,那就是与永恒的婚姻,换言之就是动力机制和吸引力之诗,琴弓之诗,他不去别的诗里。别的是愤怒。尽管这是同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诗歌是存在,但诗山也在崩塌。诗歌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对一个【人】说话,它是怎么发生的,是一个经济问题。杜根在写诗的时候并不为人写诗,并不想让人听到什么诗。因为写诗就如狄奥尼索斯对永恒回归的指环说话,你不能把狄奥尼索斯浪费在别处,浪费在写一类诗里。但这不代表狄奥尼索斯没在他一旁。杜根写的不是非诗,而是关于诗来到了它的不可能性的门槛上的诗,写的是重压之魔。对狄奥尼索斯来说,写杜根这种诗也不是时候,永远不是时候。杜根更像查拉图斯特拉,狄奥尼索斯的代理人。
只要能倾听到狄奥尼索斯的沉默你就还是诗人,相比而言,你写的那些诗就是次要的了,它们可能就是用来崩塌的——没有人能说一首崩塌的诗就不是诗。写一首让诗山崩塌的诗也是阿兰杜根的任务。如果你像狄奥尼索斯那样说话,你可能写的是鲁米一类诗人的诗,或尼采的酒神颂歌。这是对绝大多数人和自以为地位高的知识执法者的沉默。阿兰杜根显然专注于对付知识执法者,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遵守一种古埃及修辞学规则,或者说没受过修辞学教育,这其中就包括口述并让抄写员写信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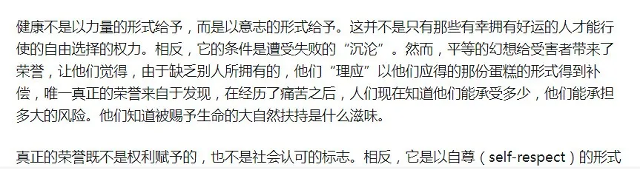
最后一点,《谢林与尼采:释放爱之神》的作者说健康的条件是遭受失败的“沉沦”,这种失败伴随着平等的幻想的失落和痛苦,却并没有因这份幻想分一块蛋糕。荣誉即这种发现,即知道自己承受了什么,也就是自尊!——一个如此清醒、理智、明白的作者,为什么要谈狄奥尼索斯。
重点是,狄奥尼索斯精神并非要给自己分蛋糕、为自己意欲强力,而是将自己意欲的东西提升到最高级形式,这不是在幻想中完成,而是在意欲中完成,所以快乐就是意欲本身,就是时空动力:
而当尼采将永恒回归解释为强力意志的直接表现时,强力意志绝不是指“意欲强力”。恰恰相反,它指的是:无论意欲什么,人们都要将自己意欲的东西提升至N次方,也就是引出被意欲的东西之高级形式,而这全靠永恒回归中的思想之遴选活动,全靠永恒回归自身中的重复之奇异性。一切存在者的高级形式一一这便是永恒回归与超人的直接同一性。(《差异与重复》p19)
“无论意欲什么,人们都要将自己意欲的东西提升至N次方”,德勒兹这句话,是AI诗人和神圣邪恶bot们永远写不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知乎上那些连抄都抄不对的大手子们,应该停止自己的无根游谈。否则迟早暴露一个不给力的神圣邪恶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