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吉利斯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问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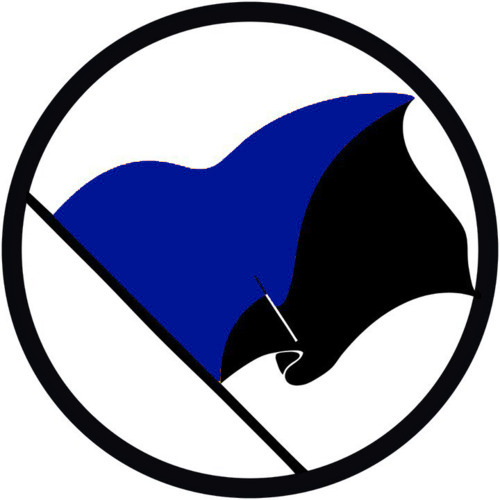
你们对技术的分析是如何比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分析更不肤浅的?
技术难道不会间接化(mediate)我们的体验,阻止我们直接地活着吗?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还有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有什么不同?
无政府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是怎么回事?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Anarcho-Transhumanism)」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在 80 年代只被极少量提及,在本世纪初期开始被公众接受,直到最近十年才真正普及。但它代表了无政府主义者圈子和理论中的一股思潮,这股思潮自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 将不断改善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愿望与不断改善我们自己、我们的物质条件和我们的身体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以来一直存在着。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背后的思想很简单:
我们应该寻求扩大我们的身体自由,就像我们寻求扩大我们的社会自由一样。
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自己是对无政府主义现有的誓言——最大限度的自由,的逻辑延伸或逻辑深化。
「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在媒体上常常被肤浅地描述为想要长生不老,或者想要将自我意识上传到电脑,或者幻想一个能够自我完善的人工智能突然出现,将世界变成天堂。有很多人被这些东西所吸引。但是,定义超人类主义的只有唯一的准则,即我们应该拥有更多改变自己的自由。
于是在这里,超人类主义开启了对固定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攻击,它属于女权主义者和酷儿理论中围绕着半机械人(cyborg)身份和「反人本主义(inhumanism)」的更广泛论述的一部分。超人类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人本主义的攻击性批判,或者被看作特定的、超越了「人类」这一偶然的物种范畴的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延伸。超人类主义要求我们超越现实的偶然性来审问我们的欲望和价值观,既不接受性别等武断的社会建构的权威,也不盲目忠于我们身体当下的运作方式。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自 1983 年《超人类宣言》("Transhuman Manifesto")开始,跨性别问题一直是超人类主义的核心。但是超人类主义从根本上扩展了跨性别解放,将其定位为我们在身体和周围世界的建设和运作中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者们致力于立即使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身体的实际项目,比如堕胎诊所、分发纳洛酮、或 3D 打印开源的儿童假肢。但是我们也会问一些激进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仅可以接受老年人的非自愿衰老和死亡,而且还会对永久消灭他们进行道德说教。
延长寿命当然不是超人类主义的全部,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表明我们已经开展了斗争。而令人震惊的是,这场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单打独斗。认为客观上「美好生活」可以延续到七十至一百年,但不能再进一步延长的想法显然是武断的。然而,这样的观点几乎被普遍接受并被激烈地辩护。许多早期的超人类主义者对这种反应的奇妙和鲁莽感到震惊,但这种反应说明了人们是如何因为害怕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生活中的常规假设,而成为现有不公正现象的坚定支持者。就像人们会为强制性服兵役和为食物谋杀动物辩护一样,对死亡的辩护显然是防御性的合理化:
死亡赋予了生命以意义。
-
70 岁时的死亡是如何比 5 岁时或者 200 岁时的死亡更有意义呢?如果一位八十岁的老妇人能为生活和诗歌创作再活五十年,这真的会破坏你寻找的意义的根基,以至于你会谋杀她吗?
我们会感到无聊的。
-
所以让我们建造一个不无聊的世界吧!甚至都不用说无政府主义和超人类主义两者蕴含着的巨大可能性:读完世界上存在的每一本书需要花费将近三十万年的时间;世界上有一亿首已经录制下来的歌曲;数以千计的语言都具有各自的概念联想和诗歌生态;数百个领域的丰富而有趣的主题可供研究;大量的体验和新奇的关系值得尝试。至少过上几个世纪我们都能应付得来。
旧有的不变的观念会妨碍整个世界。
-
本能地将大屠杀作为解决人们观点或身份不可塑性问题的最佳手段,这是相当荒谬和可怕的。自智人诞生以来已经有超过一千亿人死亡,在他们内心的一切突然熄灭之前,他们充其量只能传达出他们的主观经历、洞见和梦想中最微小的一部分。人们说,每一个老人死去,就好像一个图书馆被烧毁;于是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已经损失了一千亿个图书馆。毫无疑问,我们可能会有无数种生活和改变的方式,但如果认为当前标准的突然、大规模和不可逆转的损失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是普遍完美的,那就真的很奇怪了。
这些是说明性的例子,它们触及了超人类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义延伸的核心:要求未经审查的规范或惯例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挑战原本可以被接受的事物的能力。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打破了更多的我们对世界的操作性假设,与此同时它寻求扩展和探索可能性的范围。激进主义就是把我们的假设和模型强加到陌生的环境中,看看是什么出了问题,从而更好地澄清什么是最根本的动力;而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试图通过这种澄清来促进无政府主义的发展——使它成为更好的战斗形态以应对未来;使它能够在任何情况,而不是仅仅在高度针对于特定情况的环境下战斗。
可以很容易地说:「所有这些遥远的科幻小说般的可能性的讨论,对于我们目前的斗争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分散注意力。」我们当然不主张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日常抵抗和基础设施建设,但为我们赢得最大进步的往往正是超前的思考。事实上这是有依据的,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许多效力都来源于我们的正确预测;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虽然今天的互联网显然是重大冲突的发生地,但它提供的许多自由仍然是几十年前由激进分子所赢得的:他们先于国家和资本主义赶上之前就已经在描绘某些事物的重要性和战斗的后果。
另一方面,如果说过去两个世纪的斗争对我们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激进分子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对事物做出反应。我们缓慢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花上至少十年的时间来尝试各种方法,选择好的方法,然后推广它们。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摒弃未来主义,而只是耸耸肩说「我们将通过实践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如果真的有什么灾难性后果出现的话,我们用试错法解决它,因为我们真的没时间忍受长达多年的问题排查和反复失误。」
许多人终于意识到,我们应对方式简单,适应时间长,这往往使得我们对当权者来说是可以预测的。我们本能的短视应对措施已经被纳入到他们的计划中,我们的斗争实际上像社会的减压阀一样作用。
在「自我」和「个人」没有明确定义,传统的自治诉求落空的背景之下,试图审问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的真正含义似乎是离奇和荒谬的。有人可能会拒绝认真考虑大脑连体双胞胎的问题,认为这些使用怪异的代词、体验过多核思维的人是「无关紧要的」和「边缘的」,并认为脑对脑的共情技术太遥远而不值得谈论(当然他们不会在乎那些已经被使用的、功能有限的原型)。但是,对任何超越当前特定经验的东西的不屑一顾,最终会把无政府主义限制在狭隘的环境下,让它成为一种肤浅的、即将过时的历史趋势,就像雅各宾主义一样——我们既不能在更广泛的情形下谈论它,也不能宣称它的道德立场有任何深度或者根基。如果我们再等上一百年,无政府主义将会变成那些故纸堆中的意识形态信仰之一:依附于旧的理论框架,拒绝更新自己来适应技术上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样世界将会损失很多。
然而,澄清一点很重要:积极地考虑可能性并不等同于目光短浅的预言。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者们并没有错误地要求一个特定的未来——制定一份蓝图,要求世界遵守。相反,我们提倡的是为未来赋予多种可能性。
关注未来不会让我们失去现在吗?
如果我们直接活在当下而不反思,我们就不会有自我意识。心理递归(mental recursion)——对我们自己、他人和我们的世界进行建模——是意识本身的核心。将思想定义为思想的正是它抢先一步地思考一些步骤的能力。我们不能只是像石头一样,只顺着最陡的斜坡往下滚,而是要把握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选择的格局和可能的路径,有时甚至需要选择那些不能立即满足我们的道路。
当然,是的,不脚踏实地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你做得愚蠢,一切都会是有危险的。未来主义绝不要求与当下的斗争脱节,但它的确会影响我们当下所优先考虑的事情。例如,我们会拒绝接受一项在短期内能改善我们,但严重阻碍我们未来的斗争能力的改革。自由主义者们以忽视未来而闻名,凯恩斯(Keynes)的名言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他们用这种态度来为诸如生态破坏和赋予国家更多的权力来控制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短视行为辩护。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我们的确必须要在短期内提高实力以保持斗争的进行,但我们必须总是明白代价是什么。否则,剩下的就只是支持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家。
这并不是说假设即使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某种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中去时,我们也无法得到它。它会实现,如果它实现了,的确会改善我们的生活;只是这些改善是有极限的。而且一旦实现,它的威权倾向可能会加深,使得后代更难以推翻它。
同样,文明的永久崩溃可能会改善(极少数)幸存者的生活,但它将永远限制我们对某些缺乏的自由的选择和渴望。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为抵抗提供了哪些见解?
如果法西斯主义如此强大,为什么它还没有完全胜利呢?那时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比现在更糟。尽管我们的敌人为它付出了很多东西——他们付出了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强制力量、所有的思想和基础设施控制、所有的系统性计划和监视;尽管人类的默认思维倾向于认知谬误、残暴和部落主义——他们还是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明显的阻碍。而那些试图更直接地拥抱威权主义力量的社会或运动都失败了。尽管我们有着那么多的缺陷和不完美,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那些忠于绝对权力、盲目服从和质朴暴力的人不胜枚举,然而我们却挫败了他们的野心、超越了他们的世界观、阻碍了他们的竞选活动、破坏了他们的项目,创造性地反击、抢占了他们的先机,从他们的脚下改变了格局。
我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自由的人是更好的发明家、更好的战略家、更好的黑客和更好的科学家。有关权力的那些意识形态(或者不如说是传染性的精神病)失败的地方在于它在利用复杂性的手段上的固有缺陷。权力天生就要限制这种可能性,自由就是释放这种可能性。
拥有更多的可供使用的工具,使得我们有了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式。虽然某些工具提供的「选择」可能是肤浅的、没有因果深度和重大影响,或者选择某些工具会在其它方面缩小选择范围;但最终,如果不能不断地扩展工具集,就无法不断地达到最大限度的自由。
利用这些工具扩展的自由使得攻击者能够胜过防御者。当有更多攻击和防御的途径时候,攻击者只需选择其中的一种,而防御者就需要防卫所有。这使得对刚性的扩展机构和基础设施的防御越来越困难。
于是,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看,技术发展最终趋向于赋予少数群体抵抗统治的力量,并且使得共识和自治的文化习惯越来越有必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拥有否决权。
同样地,信息技术在社会文化的复杂性提升的方面也产生了正反馈。虽然早期原始的信息技术(如广播和电视)被国家和资本所控制,并形成了垄断的基础设施,发展了单一的文化,但随着「互联网」如此快速的发展,我们已经模糊了各种各样的技术的界限,以至于能够对此产生抵抗,反而促进了高度复杂的流动话语(fluid discourse)和亚文化(subculture)的发展。
这提供了惊异的抵抗来源,因为它使得大规模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文化潮流的变化如此之快、如此多样、如此偶然,以至于政客和企业家在试图利用它们的时候越来越困惑。
在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形成的过程中,协作性的反馈使得技术见解和发明增长得太快从而无法预测和控制;而我们对社会文化复杂性的反馈构成了社会奇点(social singularity),一种对技术奇点的反映。
硅谷(Silicon Valley)正拼命地试图避免广告行业的净利润下降的未来。自从互联网问世以来人们变得越来越明智,广告商对整体能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只有更针对个人的扩展活动——企业试图加入模因(meme)游戏,或者付钱给 Instagram 上的青少年名人,让他们推广产品——能被认为对年轻一代而言勉强有效。但这些活动的收益显然在不断减少。像 Doritos 这样的商家不会试图浪费精力,把诸如一个 30 人组成的极度复杂的青少年亚文化团体作为推广的目标。
你们对技术的分析是如何比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分析更不肤浅的?
超人类主义并非声称,所有的工具和它们的应用在所有的情况中都是完全美好的,没有问题需要被考虑、引导、拒绝、挑战或改变。超人类主义也并不是拥抱所有的现有工具的基础设施和规范。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技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积极的,并不认为工具永远不会有偏见或倾向,或者应该强行发展某些特定的「更高」技术。相反,我们只是认为,人们在与世界交互的方式上应该有更多的代理权和选择权。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更多的信息和可供选择的工具。因为「技术」在最广泛的情况下,指的是做事的任何手段;而自由的定义即是你有更多的选择或手段可用。
我们意识到尽管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背景复杂的情况,但归根结底,我们希望的是在生命和宇宙之中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就像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我们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不同的策略一样。有时某种策略或工具更适合某样工作,有时不是。但扩大自由最终要求我们扩大技术选择。
我们目前的状况最令人沮丧的是,技术被压抑得如此厉害,从而只有单一的技术文化被允许存在,通常还带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偏见。一方面这是通过压制和抹杀更简单或更原始的技术而实现的,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法律和其他各种不公正现象,技术的发展被恶意地放慢或削减了。同样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条件歪曲了技术所能取得的利益,从而歪曲了投入研究的领域。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发明天生就是腐败的或者无用的。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从头开始,忽略沿着我们的轨迹积累的所有发现和知识。
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社会中,许多标准化的工业和商品形式在解放的世界中将是不可持续的、不受欢迎的。
例如,制造光伏太阳能电池板(photovoltaic solar panel)的方法有数百种,但当中国利用奴隶劳工和土地征用权来占领、夺取和毒害大量土地时,最终会降低某些稀土矿物的成本,从而使资金更多地流向使用这种人为造成的廉价稀土的光伏方法的研究,而不是那些使用更常见的材料的可行的替代研究分支。类似的,两个世纪前奥古斯丁·穆肖(Augustin Mouchot)在世博会上展示了一种功能齐全、(在当时)性价比高的太阳能蒸汽机——仅仅使用了几面镜子。如果不是英国赢得了对印度的战争,使他们能够奴役大量人口开采煤炭从而大幅度压低煤炭价格的话,这种蒸汽机就可能被投入大规模生产。
这些不是无稽之谈,而是历史事实。制度暴力常常改变某些研究领域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的直接盈利能力。取代了加拿大矿工的是在可怕的露天钶钽铁矿场工作的刚果奴隶。
原始主义过度简化了情况,认为现有的东西必然是实现某些技术的唯一途径。它还常常暗示一个单调的线性发展过程,其中一切都依赖于其他一切;忽略了发展的道路上往往存在着的极大的自由度和选择的多样性,并且没有深入研究重构(reconfiguration)的巨大潜力。
不管怎么说,你们是反对文明的吧?
关于「文明」的任何讨论都必然涉及过于笼统和过于简单的叙述。我们的实际历史比任何简单的历史力量所解释得都更加丰富和复杂。权力系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并且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社会、文化、人际关系和物质基础设施的每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要谈论某种特征性的或者基本的「城市文化」,那么说根基在于权力就是预设了结论了。
从狩猎采集的时代以来,在每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强迫性的动力。虽然规模较大的社会能够自然地使得统治的因素更加显眼,但这并不是社会所固有的。
在已被记录的历史中,不同城市的内部等级和与周围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各不相同;许多城市的文化没有留下等级和暴力的痕迹。应当记住按照定义,更倾向平等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城市社会不会浪费能源建造巨型古迹或者发动战争,于是自然不会在我们获得的历史记录中显得那么突出。另外,由于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压迫性的全球政权之下,显然所有自由社会都已经在某个时刻被征服;当然我们知道,胜利者经常会故意破坏所有记录。同样,非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学家也跳出来假设,即使在像哈拉帕(Harrappa)这样平等主义和和平的城市文化中,任何社会协调或技术发明的存在都证明了某种类似国家的权威的存在——即使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事实如此,而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事实与此相反。
早在农业发展之前,一些地方如不列颠群岛就出现了城市集中的现象。的确,在全球的许多地方,土地无法支持起永久性的城市;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人们能够管理好,他们就努力地聚集在一起。早期的社会可能既是狩猎采集的社会,也是暂时性城市的社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两者之间来回转换。
这与把城市仅仅视为财富和权力的完全失控的集中——一个简单的恶性错误的说法并不相符。如果城市真是个坏主意,为什么有其他选择的人总是自愿选择它们?
答案当然是,人口的大数量会增加个人可用的社会选择,从而扩大了关系选择可能的多样性。
比起局限于一个或者周边的两三个一两百人口的部落来说,生活在城市使得人们能够与超越了他们偶然的出身的人亲密地结合,通过选择而有机地形成属于自己的部落;或者更好的做法是,摆脱封闭的社会集群的局限性。没有充分的理由强迫你的朋友也成为彼此的朋友。城市使得个人能够形成广泛的人际关系,延伸到更大、更丰富的网络之中。
这种世界主义使得我们能够产生、并鼓励我们产生超越部落或民族对立所必需的同理心。它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实现了非凡规模的互助(mutual aid),并帮助繁荣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文化和认知生态系统。如果有什么单一的特征能够定义「城市文化」或「文明」,那么它就是一种将复杂性和可能性释放出的、狂放的无政府状态。
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充满相互联系的、世界主义的世界,但没有现在已有的「文明」所具有的集中化和静止性特征。我们要实现城市的前景和巨大潜力,正是这些前景和潜力引导着人类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自愿组成城市。
当文明的崩溃在所难免的时候,又为什么要在乎呢?
诚然,我们目前的基础设施和经济难以置信地脆弱、具有破坏性、不可持续——它在许多方面服务于压迫性的社会制度,并与之交织在一起。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可能。我们的世界文明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整体,而是一个由许多竞争力量和倾向组成的、广阔而复杂的战场。
所谓即将到来的崩溃的「必然性」本身是站不住脚的。任何大量地简单技术发展就可能破坏它的轨道。例如大量廉价的清洁能源,或者大量廉价的稀有金属;任何一项都会导致另一项,因为廉价的能源意味着更具成本效益的金属回收,而廉价的金属则意味着更便宜的电池和对风能等能源的更多使用。地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例如一些大公司正在争夺附近的小行星,这些小行星富含如此大量的稀有金属,以至于会使得金属市场崩盘,让地球上的所有矿山都关门。
并且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文明崩溃不太可能使我们回到田园诗般的伊甸园。许多权力中心可能会幸存下来,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技术能倒退回铁器时代之前,数十亿人将会惨死,而生态破坏的突然爆发也将令人难以置信。事实甚至证明,北纬森林的扩张最终将导致全球变暖的恶化,因为树木并不能很好地汇集碳,而地球反照率(albedo)的变化(来自较暗的森林)会使它吸收更多来自太阳的能量。
不管有多大的可能性,我们都必须与崩溃带来的巨大浩劫作斗争。我们有义务奋斗,有义务在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环境中取得一些代理权,并为此承担责任。只有科学和技术才能使我们修复像撒哈拉沙漠这样的古老灾难,消除恐怖,使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重新焕发生机。
但是绿色能源和绿色技术难道不是一个神话吗?
这是错误的。如果你深入阅读有关绿色技术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从事绿色技术研究的科学家并不是某种系统地忽略了生命周期分析的、目光短浅的白痴。他们确实考虑了具体的运输成本和储能密度问题。资本家喜欢在肤浅的新闻发布会上用荒谬的东西进行环保作假(greenwash),但关于绿色能源的科学论述实际上包含了极大的数量级差异。极有可能将足迹减少 100 倍或者 1000 倍,产生巨大的差异,而不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改革。人类一直在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影响,而地球的生态系统从来都不是静止的。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某种不变的、严格限制的生活方式,不是真正的零足迹,而是让我们创造力和探索在不会摧毁地球环境的情况下实现。
如果我们将现有的碳氢能源的一小部分投入到太阳能上,我们将会有足够的能量取代它。即使只使用 19 世纪初的镜子和蒸汽管道的科技,我们也可以从太阳能中获得惊人的高功率。高能电池的选择很多,还有更多的如高密度生化存储等正在开发中。与此同时,光伏技术已经跨越了所有之前假定的障碍,可用材料的种类大量增加,同时还提供了非常简单的方法和很少的生态足迹。太阳能的能量回报率(energy return)接近 12 倍,并且还在迅速上升;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西班牙等政府已经禁止了不缴税的太阳能的私人使用,以保持化石燃料和集中式电网的竞争力;他们甚至开始对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的房屋进行全副武装的突击搜查。
尽管在80年代的生态朋克(ecopunk)趋势影响下,核能与许多极端消极的因素相联系,但其中许多担忧仅仅在冷战式的核应用条件下才是有效的。在那种条件下,反应堆是高度集中、由国家运营的,而且只使用那些产生能够武器化的副产物的材料。另一方面是许多液态氟化钍反应堆(liquid fluoride thorium reactor),它们从设计上来说就不可能熔化,使用的是一种已经天然存在于地球表面上的、常被当作有毒污染的放射性材料,产生的核废料半衰期相对较短。
同样,虽然一些似是而非的「冷聚变(cold fusion)」报道,以及80年代的对正常聚变的过分热情的报道使得聚变已经成为深夜电视节目上的笑柄,但它仍然是合理的且已知的清洁能源的极好来源;聚变受到的只是工程挑战的限制,而不是任何基础科学问题的限制。聚变在近期也取得了一系列初步的成功,跨越了很多标准。
尽管所有这些技术都可能提供廉价的能源,但此时我们逆转全球变暖的唯一方法是使用负碳技术(carbon negative technology),即留下固态的碳作为副产品的技术。从古老的气化反应(gasification)技术到各种藻类养殖方法在内的很多方法都已被证明有效。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些技术都没有被广泛采用。国家暴力补贴了我们极其低效的基础设施,因为它们支撑着中央集权的大规模经济实体。同样,我们目前的大部分能源都消耗在战争和无聊的事里,供需严重扭曲;某些公司和行业已经系统化地转移了他们的环境成本。
事情不必是这样的。技术发展从本质上扩展了选择的范围;所以我们最近的技术创新已经从粗暴的大规模集中式基础设施结构,转为了 3D 打印和开源(open source)这条路线,转为了有机、分散和可重构的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引用目前还不存在的技术,难道不就是异想天开吗?
在「物理上可行但尚未设计」和「谁知道呢」之间有着深刻而至关重要的区别。
比方说,还没有人建造过一个颠倒的树屋,甚至没有人设计过它。但是你会立刻意识到,这样的事情是可行的。人们必须起草一份设计方案,想出好办法来应对某些挑战(比如朝上的结构的底部或者说「地板」显然必须衬有某种防水材料),然后再建造它。上下颠倒的结构可能会显得很古怪,但你的孩子会从中得到乐趣。但重点是:我们不必争论建造它是否是「不可能」的。问题本身是工程/建筑/做些数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完成的时间可能会比我们预计得更短或更长,但它们是可以完成的。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大多数事物都落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它们不可能被物理学、数学、化学之类的东西所阻止。比如说,我们不是在谈论虫洞。这些问题只是工程问题,尽管它们具有挑战性。小行星采矿之于当下,就类似于人造卫星之于50年代。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知道它会有回报,我们只需要先他妈的在路上完成一大堆工作。
所有这些显然都不是「异想天开」。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都是非常简单、非常保守的那种「嗯这显然会是可能的」之类的东西。估计它们要多久才能实现自然是主观的问题,但是若是假装工程机器人采矿将不知为何变得异常困难或者需要等量的人力才能完成,显然就变成阴谋论的科学否定主义(science-denialism)了。
技术难道不会间接化(mediate)我们的体验,阻止我们直接地活着吗?
所有的因果关系互动都是「间接」的、有中介的。空气传播着我们的声音。电磁场和所有介质介导了我们观察的能力。文化和语言决定了哪些概念可以被清晰地表达出来。
你可能认为这是个「平凡的」问题,但这是个深刻的问题。很难提供一个客观的指标来衡量什么是「更间接」,更难的是试图说明这样的指标有意义。
没有「直接体验」这回事。要看到任何东西都需要大量的处理,因为原始信号会被视觉皮层中的柱状神经(neural column)处理成更抽象的信号。可以从视错觉和模式幻觉(patterned hallucination)中找到这种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假象。反过来,我们的经验决定了模式识别回路具有哪些优势。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直接」体验就是完全不体验或不思考。
当然,人们可以试着区分「人造的」中介和非人造的中介,但这样的区分与我们体验事物的本能或准确性没有根本的关联。虽然你的社区 WiFi 网络被窃听或审查是另外一种特性的危险,但是这样的干扰或破坏会以各种方式适用于我们的所有交流手段,包括文化和语言结构。
谈论「更」间接而不是有不同背景利弊的不同特性,是没有意义的。甚至约翰·泽赞(John Zerzan)都戴着眼镜,以提高他的整体视觉体验能力和与周围世界互动的能力。在许多方面,现代技术都可以用来扩展我们与自然、我们与彼此接触的深度和丰富性。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者与其他超人类主义者有什么不同?
超人类主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立场,所以有很多人都被它吸引。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令人讨厌、目光短浅、幼稚或者反动。
值得庆幸的是,相当一部分反动派最终意识到超人类主义的解放成分是多么不可分割时,他们放弃了它。「性别二元性(gender binary)的死亡?这可不是我的目的!」这些白痴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了书呆子式的法西斯主义(fascism-for-nerds)的信徒,成为了另类右翼(alt-right)的一部分,被称为「新反动(neoreaction)」。一个特别具有启示意义的反转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希望并鼓吹文明的崩溃。他们希望这会导致后启示录(post apocalyptic)的景象,而他们的生物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的荒谬观念能够在其中占据上风:「真正的阿尔法男」像军阀一样统治,而我们其余的人被用来强奸、奴役或狩猎。或者我们被迫回到部落规模的关系,更好地实现(小规模的)民族主义认同、人际等级制度和传统主义。其他人则设想的是小公司领地和某种人工智能上帝,通过阻止受压迫的群体获取、理解或开发技术,来帮助他们维持理想的等级制度。
显然这些法西斯主义者都该死。我们很高兴他们已经离开了超人类主义,并希望他们剩下的同类也能追随他们。
可悲的是,尽管那些彻底的反动派已经离开,但大多数超人类主义者目前仍然认同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类似的技术官僚权力崇拜。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佐尔坦·伊斯特万(Zoltan Istvan),他同时还在竞选总统,是超人类主义者最大的尴尬。
显然我们发现,非无政府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往好了说是政治上的天真,往坏了说是危险的地狱。但是我们也认为没有无政府主义的超人类主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一个人人都增强了身体机能的世界就是一个人人都具有超级权能的世界,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就好像每个人都有否决权一样;而不是通过多数决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的强迫做出决定。
为人们提供工具,同时自顶向下地限制或控制他们能用这些工具做什么或者他们能发明什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实施一个荒谬的极端威权的制度,压制住这些工具几乎所有的功能。这可以从互联网上的强制实行「知识产权」的斗争,或反对通用计算(general purpose computing)的斗争中看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国家主义的超人类主义者,由于他们对自由和人民大众的超级权能的挥之不去的恐惧,都无法达到超人类主义的理想。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超人类主义对我们的身体和环境更大代理权的拥抱,和压迫性社会制度对我们代理权的广泛限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会产生许多不同之处。我们显然不那么希望国家和资本家对新技术控制和开发的垄断;我们支持对他们的集中化基础设施的严肃抵抗,并为所有人解放他们的研究和工具。杀死 Google 至关重要。
最后,在非无政府主义的超人类主义圈子里,有一股相当令人失望的潮流。他们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不是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的数十亿个思想的解放和赋权。如果我们想要智能爆炸,那么更可靠、更快捷的途径就是解放并赋权那些被困在世界各地的贫民窟、露天矿山和田野中的所有潜在的爱因斯坦。此外,令人感到可怕的是,我们对人工智能的默认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如何要最有效地控制/奴役它?」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孩子,那他们理应得到同情和自由。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还有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有什么不同?
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我们的分析比单纯的政治经济学更深入。无政府主义者侧重于在各个层面上解决统治和约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宏观或制度层面的问题。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仅希望拥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且希望拥有一个没有权力关系的世界——我们的道德分析延伸到挑战权力在人际中的动态,包括更复杂的、更微妙的、非正式的,甚至双向的统治和约束关系。
尽管我们和他们一样,渴望技术的效力带来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并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垂直主义」处方。我们同样反对目光短浅的直接主义,但我们在他们的「战略」细节中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旧马克思主义的反应;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治革命/社会的精英阶层。
这种忠诚导致他们同情并误解了我们世界的方方面面,暗示某些公司和国家结构反映了必要的等级制度,而不是有系统性暴力支撑的恶性浪费,事实上在主动地压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更广泛地说,马克思主义与其意识形态分支原始主义有一个共同的令人不安的倾向,即使用诸如「资本主义」或「文明」之类的宏观抽象的神秘术语。在他们的分析中,这些实体被赋予一种代理权或意向性,并且它们内部的一切都被视为服务于更大整体的组成动态,而不是冲突的和可以重新安排的。这常常使这两种意识形态既看不到更美好世界的方方面面从旧的外壳中生长出来,也看不到那些有意义的抵抗和积极变化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并不完全是灾难性的彻底崩溃。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和素食主义(veganism)有交集吗?
非常多!无政府主义的生物黑客已经开展了一些项目,比如让酵母生产普通奶酪中至关重要的乳酶——只需将酵母放入加糖的暖缸中,它就会自己出来!比如其他一些人致力于定制藻类生产,提供比传统农业更高效的方法,从阳光中生产有用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甚至消除了拖拉机作业造成的死亡。
甚至从更远的角度来看,在使地球的大部分地区重新野化(rewilding)之后,我们对生态系统的更深入的了解可能使我们能够进行微调,以减少净痛苦。或者甚至找出如何与海豚交谈的方法,并说服它们不要成为如此凶残的强奸犯。
无政府超人类主义如何处理能力的不同和非神经典型者(non-neurotypical)的问题?
如你所料,超人类主义者和无政府超人类主义者的立场就是让这数十亿个物理和认知结构能够蓬勃发展。我们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打击和消除歧视(stigma),并约束社会规范,从而可以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下过上多样化的生活。同时,我们还希望为人们提供工具,让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思想和生活状况。应该由每个人自行决定,他们的生活中有哪些是压迫性的损害;而有哪些是他们的身份和独特的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最终,我们寻求消除「损害」和「增强」之间的区别,以及「想要」和「需要」之间的区别。任何「基准(baseline)」都不应该被严格地规范化。
为什么颜色是蓝色?
蓝色作为未来的象征有着悠久的历史。蓝色是天空和大海的颜色,是有待探索的遥远地平线。蓝色色素在自然界中非常罕见,蓝色玫瑰和蓝色花朵更是普遍地象征着人造、未来、希望和无限。蓝色是绝大多数科幻中使用的特征颜色。
蓝色还更普遍地暗示加速和速度;当观察者向某个物体加速时,所有其他颜色都会「蓝移」。
当然,我们在十五年前选择了蓝色的最简单、最明显的原因是,在无政府主义学派的色轮上,它是最后没有被使用的主要颜色。我们想以一种不遵循90年代传统的红色对绿色争论的方式来捍卫我们的想法和抱负。重要的是,我们将自己与传统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和共产主义的潮流区分开来,而又不试图否定或支配这些主义的现有表现形式。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热衷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和布克钦(Bookchin)的非常经典的抱负;另一些人则是后左派(post-leftist),强烈批判组织主义(organizationalism)和意识形态僵化;其他人来自诸如互惠主义(mutualism)的更加市场导向的传统。但这其中许多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物理条件和技术手段的共同关注。
最有趣的辩论最终不是关于19世纪的经济体制,而是关于我们想要如何在宇宙中生活,以及我们对宇宙应该有什么价值观。在绿色和蓝色的辩论中,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原始主义者使用了大地的颜色,而我们使用了天空的颜色。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下,颜色的象征意义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很多国家——除了一些相当引人注目的例外——保守派通常使用蓝色来代表自己。同样在国家主义者的政治视野中,有些可悲的混蛋也使用了其他的颜色。法西斯主义使用黑色;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使用红色;社会民主使用粉红色。我们不觉得有任何关心我们敌人的内部配色方案的必要,就像他们也不关心无政府主义者的内部配色方案一样。我们的政治立场显然与保守主义完全相反。
[1] 戈德温经常被认为是现代第一个杰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P.J.蒲鲁东后来是第一个明确使用这个词的人。戈德温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功利主义者,但他的伴侣和爱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经常被称为第一位现代女权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女儿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经常被称为第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使他黯然失色。戈德温呼吁废除国家、资本主义和许多其他形式的压迫,但也将这些与呼吁彻底扩展技术能力结合在一起,这包括许多深远的可能性,如延长生命和击败死亡。 戈德温只是历史上众多以尖锐的超人类主义术语发言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例如,伏尔泰琳·克雷(Voltairine de Cleyre)赞扬了更大的技术自由的发展,并将最终目标视为「一种理想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将像神一样,拥有享受和痛苦的神力。」
